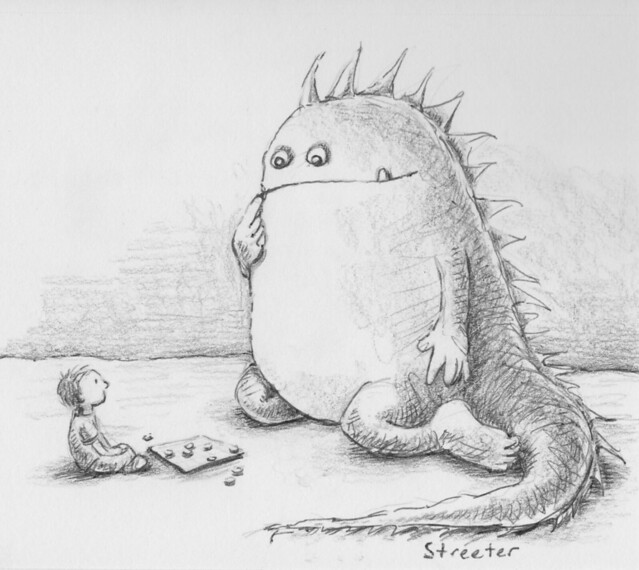|
| _fabrizio_@Flickr, CC BY-SA 2.0 |
週五夜裡往戲劇院去看
雲門的春季公演。〈迷失之影〉撼人、〈斷章〉絢美,是兩支相當值回票價的舞。步出戲院已是十點半有餘,我用計程車先送S回家。
上了車,我倆口雜,簡單交換對這齣舞碼的心得。司機突然插嘴進來:「不好意思喔,請問一下,今天是什麼表演?」
我回答,是雲門。司機點點頭,噢,雲門啊。
其時S生日將屆,恰巧慣用的香水已經用罄,這幾日四處研究,正打算挑一瓶新香送她當作禮物,簡單交換心得之後便自然聊起這幾天打量過的香水來。說香奈兒 Chance 粉味太重、凡塞斯玫瑰香味那支卻又有點太俗氣了、雅詩蘭黛純粹香很不錯但和S調性不合、而同牌的歡沁有果香的那罐似乎就恰到好處。......
司機冷不防又插進我的話來:「你對香水很有研究?」
我愣了一愣,回答,呃,沒有,是要挑一支作禮物送人啦。所以最近有隨意看看。
「那你看看我這罐怎麼樣──這罐香水跟了我二十幾年囉。」語畢,隨手從一旁取出了一個髒髒的白色紙盒,遞給我。
我打開來,裡頭是一只扁方形、有蓋的玻璃瓶,瓶中搖晃著三分之一滿的茶色香水。
「你可以打開來聞聞看,這是很好的香水。一聞過,就沒辦法喜歡別的了。」
跟隨別人二十餘年的香水瓶我不敢隨意打開,僅讓瓶蓋處湊近鼻尖,輕嗅了一下,是相當濃郁沉穩的花香。S接過也嗅了一下,點點頭表示的確是好香。我們把玩著香水,一面東問西問,我這香水的門外漢當然問了些笨問題:這現在還買得到?
司機笑著露出「啊原來你不懂」的表情回答,有啊,當然買得到──「只是這個瓶子啊,是我在沙烏地阿拉伯當工程師的時候買的,現在,再也找不到囉。......」
那現在賣的,味道還一樣嗎?
「當然一樣,不一樣怎麼可以──只是,瓶子就不一樣了。」
正要說下去就到了頂溪站,先靠邊停車讓S下車回家,我才請司機掉頭開回市內。
短暫的沉默後我接續話題:所以,這是在阿拉伯的百貨公司買的?
司機見我興致勃勃,話匣子大開,「是啊,是在那邊的百貨公司買的勒。你不知道,在那邊工作真的很無聊很無聊──」
什麼都沒有,沒有酒店、沒有酒吧、沒有電視、不能玩女人──噢,除非你要剛好遇到外國的郵輪才有辦法。不過那要靠門路的,有門路人家才會帶你上去──完全沒有電視喔,應該說,沒有電視臺,就只能看那邊美國工程師帶去的錄影帶。當然錄影帶有很多那種有的沒有的,可是你知道男人就是這樣。不過外國作的影集真是好啊,還有誰誰早年拍的那些,那些真的是藝術、是藝術,你不要拿情色的眼光去看待他。
那時候臺灣在各個國家都有農技團啊、工程團,我就是跟著他們過去的。可是除了工作之外真的很無聊很無聊,看錄影帶、看書、睡覺,頂多就是那時候還是年輕小夥子,就開著車子去馬路上飆車──為什麼可以飆車?因為有時候啊開了好幾個小時都看不到一個人勒!哪會什麼撞車危險什麼的。還有啊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百貨公司逛街。這說起來也是機緣巧合啦,就剛好在那個地方遇到這個香水,我一聞、一用就改不掉了,其他的香水根本就用不習慣。
阿拉伯是一個回教國家啊,規矩很多,對自己國民的保護也很多很多,像我們外國人啊如果要在那邊開店,一定要找當地人合資才可以,然後要住多久多久才可以在銀行開戶。還有啊,聖地麥加那個地方,你如果不是回教徒,你開車不能進去麥加,大概是怕污染他們的聖地,所以欸,這裡不能過,你從旁邊繞過去,以前就鼻子一摸就只好繞過去啦。還有啊,有時候在商店買東西,回教徒一天有五次要這個朝拜,時間到了就開始廣播,然後所有的店家都要關起來,我們客人就被趕出來──剛去的時候還覺得莫名其妙,又不知道他在講什麼,就只知道被趕出來──啊如果店家不關門怎麼辦?就有人會拿鞭子出來打啊,是真的打勒,這不犯法的喔。
啊對了,那時候啊,還有一個很悶──不是我在講,那個時候真的很悶,什麼都沒有──很悶的娛樂就是聽卡帶、錄音帶。
說到這裡,司機興致一來,「我我放給你聽。你們年輕人可能不喜歡聽了,不過你聽聽看喔。」說著汽車音響處突然像某種機關般緩緩降下,露出裡面有一個放卡帶的直孔,他隨手點了一點按了一按,音樂便流動起來。
他一面說,這是我們那個年代很好的音樂,就是一種輕音樂,或是叫阿哥哥(agogo)。
我躺在椅背上,看著這城市在窗外不斷流過的燈火,安靜傾聽這沒有歌詞、旋律甜美的音樂。司機不忘插嘴解釋,這卡帶,也跟著他二十幾年了,你看,音質還是這麼好!其言不假,錄音帶的聲音毫無雜質,旋律乾淨而動人。
曲畢,他甚至將錄音帶取出,遞給我看。那是一只非常素雅的錄音帶,白色的塑膠殼上貼著藍綠色的貼紙,因為年代久遠而輕微發皺。上頭除印有「PHILIPS 」字樣外,別無其他點綴。
「飛利浦?」我問。
「是啊,就是飛利浦出的一系列很棒的錄音帶,我全部保留到現在,開車的時候偶爾也會聽。怎麼樣。很棒吧。」
我幾乎還說不上話就被截斷,似乎因為目的地將至,司機迫不及待想將故事的結局說完,「我也有一個兒子,現在二十七歲了,是從阿拉伯那邊回來之後才生的。」
──啊,我到了。前面巷口靠右就可以了。
司機笑著點頭說,好的。
下車時我問他,要開到幾點?他仍是笑笑地回答,快了、快了,就要回家了。我住在淡水,開回去還要一段時間勒。
最後我也向他說謝謝,也點點頭,才把車門關上。
謝謝。真的謝謝。
目送計程車離開的時候我非常由衷地說。
返家後我查到
這段資料:
根據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在台北簽定的「中沙農業水利合作協議書」,於六十八年二月在沙國農業與水務部(農水部)正式成立。我政府派遣卅四位農業及水利專業技術人員,以應聘方式分派到農水部有關單位服務,以配合沙國經濟建設之發展。
若是返臺後才成家生子,而兒子今年二十七歲,意味著他約於民國六十九年左右返臺──所以或許我在那個夜裡所遇到的司機,正是臺灣首批到阿拉伯擔任技術外交工作的三十四人之一?
民國六十八年二月,我國第一批技術人員才抵達阿拉伯。一兩年後他便返臺,成家、生子,轉眼二十七年過去,他此際儼然已五六十歲之譜,而在這數十年的人生裡,他不斷對著過往乘客訴說的,卻是二十七年前那短短一年裡、在那個「真的真的很無聊很無聊」的遠方國度所發生的點點滴滴;在那臺小小的計程車裡,他幾乎是迷戀地收藏著關於阿拉伯國度遙遠的記憶,用著二十年不曾改變的香水,聽著二十年不曾變質的音樂,彷彿關上車門,這個世界還停留在他年輕時那個黃沙滾滾、舉目無親的異國歲月──我不禁揣想,那個「真的真的很無聊很無聊」的回教國度,究竟深藏著怎麼樣的記憶?
那罐他引以為傲、展示再三的香水,前味是香油樹花和橙花、中味是茉莉與玫瑰、後味則是檀香木和波旁香根草。
──香奈兒五號。
是女香。
我想起他司機前座上的執照卡,應寫有他名字的地方一片空白;想起他不斷說著的,「這瓶子,再也買不到了」;想起他一直呢喃的,「這香水,用過了,就沒辦法再喜歡別的囉」;想起他說,遇到這支香水,是「機緣巧合」;想起他不住重複的,二十幾年了,全都二十幾年了;想起他聽到S忍不住問「您有太太嗎」時沉默不語的瞬間;想起他對我說話時,在燈下興奮又滄桑的表情。
二十幾年了。
沙烏地阿拉伯。
香奈兒五號。
我日後常想起這個司機,想著他沒有對我說出口的,會是什麼樣的故事。
20090407@ptt2